

“噪音就像是神话中托尔的对手,它看上去轻微,甚至乍看之下很虚弱,一旦你想动一动它,你会发现自己正在举起整个世界。”这是加列特·基泽尔在《噪音书》中所描绘的,“你可能对噪音不感兴趣,但噪音对你兴趣正浓。”比起世界上每时每刻正在发生的灾难,噪音总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是可忽视的。我做声音研究,常常不被理解。声音?它听起来既不比文学、哲学、历史更深刻,也不比政治、经济、文化更重要。然而,声音就蕴藏在文学、哲学、历史之中,正体现着政治、经济、文化。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中心主义的时代,声音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作为声音一部分的噪音也是不重要的。当你这么想的时候,或许你正在饱受着睡眠问题的摧残,而你却不知道这是由于你所处环境中的噪音造成的,它正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展开攻势,你的身体和精神为之付出代价,而你却对它一无所知。即使你认为噪音是个轻问题,这也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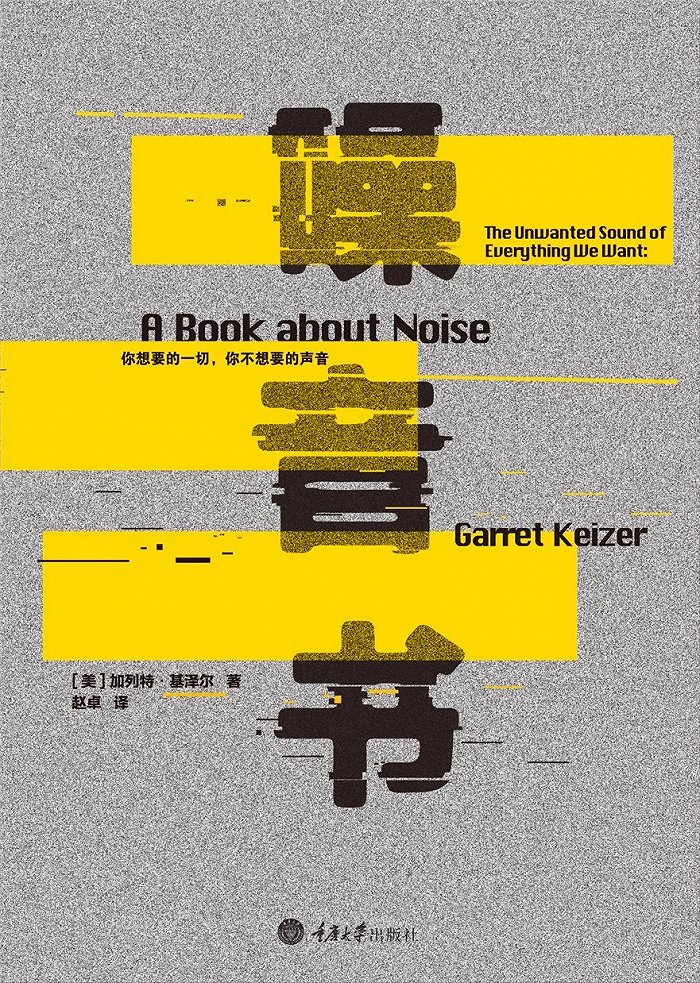
加列特·基泽尔著,赵卓译:《噪音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来源:douban.com)
噪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定义是有争议的。有的人认为噪音是不想要的声音(unwanted sound),有的人认为噪音就是污染物。在我看来这并不冲突,我认为噪音可以有两种阐释方式:客观的噪音,主观的噪音。
主观的噪音有两种阐释:一种是不想要的声音,另一种是不合时宜的声音。这两者依据不同的声音语境和个体的主观感受而定。
不想要的声音,亦即在某一声音语境中不希望它存在的声音。比如,弹钢琴时脚踩踏板的声音,在不同声音工程师的手中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认为这是钢琴演奏的一部分,踏板的声音能够更好地展现钢琴家对于某首作品的理解;有的则认为这不是钢琴音乐的一部分,而是一种不想要的声音并予以消除。
不合时宜的声音,顾名思义,声音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场合。比如,当我非常喜爱的音乐在半夜两点钟以高分贝出现时,也是一种噪音;再比如,电影院、音乐会、讲座进行中的对话声、铃声、咳嗽声等,都属于不合时宜的声音;换一个语境,这些声音不一定是噪音,而在某些特定的声音语境中这些声音成为干扰。在这些情况下,声音本身并没有变化,变的是声音出现的语境。
对于噪音的理解往往是与个人的喜好相关联的。比如,此刻我写作这篇文章所使用的是机械键盘——尽管,工程师创造出了把键盘敲击声降到足够低的先进键盘,但我在写作时仍然偏爱使用机械键盘,因为机械键盘敲击时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噪音”让我有书写的感觉;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声音,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一种不想要的声音;即使对于喜欢的人来说,当在安静的图书馆阅读时传来邻桌噼里啪啦的声响,恐怕也是一种噪音,这是不合时宜的声音。再比如,金属音乐对于某些人来说是音乐,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噪音;反过来,噪音音乐这种新型音乐形态,即便成为一种实验艺术,对于某些人来说依旧是噪音。彼之噪音,我之悦音。
在我的声音研究课上,本科生们对于喜欢和不喜欢的声音各有阐述。有学生讲,不管使用什么音乐,叫早的铃声都是噪音;有学生讲,农村砍树的机械噪音是他最爱的声音,因为会让他回忆起童年的时光;说起童年的美好,还有学生讲农村烧柴火的声音是他的最爱,一听到就联想起外公外婆给他做饭。何为噪音,何为悦音,还与记忆相关。
 星月夜,宁静的自然,永不停歇的高速路。2020年10月徐秋石摄于深圳家中
星月夜,宁静的自然,永不停歇的高速路。2020年10月徐秋石摄于深圳家中
诚然,噪音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主观体验,取决于不同的声音语境。但尽管不同人耳对于声音的敏感程度不同,人体终归有一个对分贝承受能力的阈值,超过它,会在客观上对身体和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噪音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损害听力。第一种,通过类似爆炸或者开枪时发出的剧烈的刺激性的声音;第二种,长时间暴露在强声之中,无论是主动发出还是被动地接受,声音不用太大,只要超过八十五分贝,甚至暴露在较小刺激的声音下一定时间也能引起听力损害。”而八十五分贝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噪音书》中给出了很多数据,比如,儿童玩具的音量是八十五分贝,约等于一场摇滚音乐会的分贝,约等于喷砂机工作的分贝。书中还提供了许多具体案例,阐明“噪音会引起诸多有据可查的不良的生理反应:耳聋、耳鸣、高血压、心脏病、新生儿体重偏低,甚至根据统计显示可影响寿命”。并且远不止此,噪音还会导致诸如“紧张的刺激(噪音是一种酷刑)”“干扰睡眠”“影响专注力”“精神疾病”“习得性无助”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我所谓的客观的噪音。
在基泽尔看来,遭受噪音影响的一是弱者,一是弱事。弱者,是社会中通常被忽视、被边缘化的群体。“这里的弱者,指的并不是个人能力和身体的强弱,而是指个体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高低。”受到噪音侵害的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又因为噪音一直以来是一个不被重视的“弱”问题,因此受害者往往无计可施。书中举例,她长期遭受邻居家噪音的侵扰,但她所在地区规定八十分贝以上的噪音违法,而邻居家的噪音“只有”七十六分贝,法律无法管束,只得与邻居洽谈,但对方非常强势,以暴力威胁,于是除了忍受或搬家她别无他法。这种情况此时此刻正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发生。多数案例中,对现状无能为力的受害者、受害家庭往往在习得性无助中消沉,而某些不堪侵扰者会选择以暴力的方式在解决冲突的同时,也解决了对方的生命。噪音还总伴随着暴力。
至于弱事,基泽尔所指的是“任何既不能产生新闻效应也产生不了金钱效益的活动”。听鸟鸣欢唱要让步给高楼大厦的蓬勃兴建,安稳的睡眠要让步给公路飞机的高速运转,大自然的静谧和生活在其中的所有动物——包括人——的安适在现代化、工业化、国际化的大旗下变得微不足道。
在现代化都市中,噪音与资本结盟,基本上,资本出现的地方,噪音就伴随出现。工地、工厂、飞机、火车、高速公路、商场,甚至是海洋——人类进行海洋勘测工程所产生的噪音对诸多以听为生的海洋生物造成了破坏性伤害,致使它们身体紊乱、无法辨别方向、无法猎食。人类丧失的不仅是对地球的敬畏,高度现代化的噪音已经在宇宙中唱响,海陆空三维已没有人类噪音还未涉足的空间。
 重庆的夜,灯火辉煌的背后是无限的电网及其噪音。徐秋石摄于2020年11月
重庆的夜,灯火辉煌的背后是无限的电网及其噪音。徐秋石摄于2020年11月
当谈到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最常被提到的是垃圾,准确来说,是可视化垃圾。然而,资本所制造的噪音垃圾是不可见的,只有遭受噪音足够强或足够长时,其负面效应才有可能被感知。在这个视觉中心主义的时代,一切可见的被认为是重要的,凡不可见的皆可被忽视。
噪音问题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因为生产噪音的通常是强者,是权力结构的上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看,大自然是权力结构的下端,是可以被剥削的;从资本的视角看,欠发达地区是权力结构的下端,是应该被改造的。在这种权力结构中,每一层级还可以再分为上端和下端。穷人遭受噪音的概率要远高于富人,比如,富人乘飞机买位置靠前的,噪音低;比如,穷人的居住环境更差,飞机场周边的房价更低。在这场权力游戏中,资本创造了现代化的宁静,而这是以巨大的噪音问题为代价的。现代化的宁静是可以购买的。有钱人可以花钱去湖畔享受拥有三百六十度湖景视野房间的宁静,而这背后隐藏着一个长长的噪音污染链条——在湖畔建造现代化民宿、该民宿的一系列供给、前往该地的交通工具等都在发出噪音以支撑这高昂的现代化宁静。
噪音问题之所以复杂,还在于它不仅涉及弱者,还涉及他者。不同种族族群之间的歧视和文化差异导致了对何为噪音的不同理解。例如,不少美国白人视爵士乐为噪音的主要原因是爵士乐是黑人音乐;相似地,一些中国传统音乐传到美国后也被视为噪音。噪音中的他者问题是一种全球视野下的文化霸权。
噪音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噪音的理解也是随着人类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可以想象,在远古至采集狩猎时代,能够被人类认为是不舒服的声音的很有可能是大型动物的嘶吼声、打雷、地震山崩的自然声,以及人类由于受伤或生病带来的痛苦呻吟等;这些声音要么预示着危险,要么反映着不适的身体体验。进入农耕时代后,由于技术的发展,让人们感到不适的声音发生了变化,从前被认为带来不舒服体验的声音很可能还存在,但增加了譬如砍树产生的声音、马车经过发出的声音、杀鸡宰猪发出的声音等,人们开始用“噪音”一词形容这些不想要的声音。至此,被认为不舒服的、不想要的或干脆称之为噪音的声音谱系,大致是线性增长的。但是,当技术发展至工业时代后,噪音被彻底改变,并且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仅是由于噪音的量成倍增长,更是因为噪音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现代社会中的噪音问题是一个以电为核心的技术问题。可以说,整个现代社会是由技术设备所支撑的。声音史家艾米丽·汤普森(Emily Thompson)在《现代性的声景》(The Soundscape of Modernity)一书中讲述了现代社会的声音景观被科学家和工程师所研发的电子交流设备彻底改变。现代社会的噪音首先来自电,即使再小,每一根电线都会产生电子杂音,而整个人类世界是由一个庞大繁复的电网编织而成的,有上万亿条线路在同时运转,不仅有每一根电路产生的杂音,还有各个电路之间冲撞产生的干扰音。整个大自然被一个巨大的电网所包裹。过去,传声器、扬声器、扩音器、吸声材料等声音设备基本上只出现在录音室、音乐厅等特殊场所,然而伴随着现代化建设,工程师将声音设备普及到每一个场所、每一条马路、每一栋楼,乃至每一个家庭中。声波上天入地,不仅在空气中、水中传播,更在建筑物、公共设施和每一个人工造物中反射和传播。整个大自然成为一个大型录音室,大自然被声音装置化了。声源无处不在,声音装置无处不在。此时,大自然的声音景观已经被彻底改变,纯粹的大自然的声音正在逐步消失。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鸟鸣、风吹、雨打,要么是被声音技术加工过的,要么是被技术物反射过的。纯粹的自然声音或许只能在远离城市的自然保护区内,且当四周没有公路、当上空没有飞机的时候,才有可能被听到。人们对噪音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在过去惹人厌烦的蝉鸣声、马蹄声、砍树声已不再是日常生活中所能听到的声音,也不常再被称为噪音。
 大自然被声音装置化;再美的景,景中满是技术物,技术物无不时刻发出声响。2020年9月徐秋石摄于深圳家中
大自然被声音装置化;再美的景,景中满是技术物,技术物无不时刻发出声响。2020年9月徐秋石摄于深圳家中
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电音化的世界。自爱迪生发明白炽灯以来,白炽灯的杂音就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在全球各个角落响动。一个现代都市的家中,基本标配是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等,这些电器设备的背后是一条条电路、一张张电网,这些电器无时无刻不在发出低分贝的杂音,除非断电。我们的生活在不断地被各种由电支撑的高新技术所丰富,加湿器、除湿器、空气净化器、洗碗机、消毒柜等等,日常家庭已逐步走向智能化,而智能化的背后是庞大的电网及其杂音在支撑。
的确,新技术的不断革新在减弱着旧技术的噪声,比如飞机、高铁和汽车。但是,噪音整体却在呈量级增加。基泽尔在书中举例,一架今天的飞机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第一代喷气客机安静得多,但是,今天成千上万架“安静”的飞机共同形成的噪音景观一点也不比那时候弱。技术进步的同时,量在成倍递增。技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更多力度更强、更为致命的问题。所有更新、更高级的技术发明都产生了新的噪音。每一项新技术所产生的新噪音可能会远远低于从前,但是,技术的增长总量和增长速度则远远大于从前。
于是,我们的身体在不断地自我调节,以适应无处不在的越发嘈杂的各种声音,如同很多动物因为受到噪音的影响而改变行为模式,人体也在以不自知的方式做着调整;如同很多动物的防御能力因为噪音伤害而大大降低,人体的某些功能也在不断退化;技术在不断拓展着人类身体的极限。
《噪音书》称,我们身处在一个“耳鸣的时代”。如今,噪音的产生已经不再需要声源了,因为你的耳朵就是噪音的声源。耳鸣已成为现代病之一,少有人没有体会过耳鸣,不乏严重者需要靠药物治疗。在工业化时代,我们听得太多,多到没有听不见的权利了。
噪音的对立面不是静默,但是噪音总在剥夺寂静的权利。
 大自然的录音室化,城市已不见纯粹的自然;看得见的是融为一体的城市与自然,看不见的是业已遭到破坏的自然声景。2020年8月徐秋石摄于深圳家中
大自然的录音室化,城市已不见纯粹的自然;看得见的是融为一体的城市与自然,看不见的是业已遭到破坏的自然声景。2020年8月徐秋石摄于深圳家中
寂静与资本增长是相互排斥的,若想削弱噪音,就要削弱商业。据基泽尔提供的信息,对安静环境的需求总是与为利润而建房相冲突,因此当里根政府奉行崇商政策时,在一九八二年削减了美国噪声消除与控制办公室(U. S. Office of Noise Abatement and Control)的预算,自此,美国的噪音相关政策彻底发生变化。在大科学时代,资本的运营和增长是建立在科学的技术(scientific technology)的应用和发展之上的。建住宅楼、商业圈、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等等都是为了提高效率、获取经济收益,这一切皆以科学的技术为支撑,并以制造更高量级的噪音为结果。
如果说,按照现代化、工业化、全球化所吹嘘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让人类更加幸福和自由,那么我想问:
听音自由是个体的权利吗?当我阅读《噪音书》时,窗外平均每三分半钟传来一次的城铁声不住地打断我的思绪,由远而近,由近及远,我不住地担心长此以往这种噪音会对我的耳朵和身体造成负面影响;更让我担心的是,我似乎已经习惯于这种噪声了。我所租住的房子位于一中档小区的最高层,紧挨学校,毗邻城铁;租房时虽担心噪音问题,但考虑到是在最高层,且地理位置优越,便将就了。起初,清晨城铁开始经过的时刻就是我醒来的时刻,渐渐地,我的双耳及身体便适应了这种规律性噪音,城铁声不再能吵醒我,白天生活也听它为寻常。这种技术噪音对人体的驯化令我担忧。我已不再能明显地感知到它,然而它却以一种更深入的方式侵蚀着我的身体。我还不属于住在地铁旁的穷人——如今建在地铁周围的房子是好房子,尤其在大都市,地铁旁的房子价格更贵。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房价的评估也已从对噪音的担忧转变为对效率的追求。在研究噪音问题之前,这城铁噪音是可以被忽视的,如今它却变得非常刺耳。城铁的噪音是客观的,我的感受是主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主观对于噪音的消化就能够降低客观的噪音对我身体和生活的侵害。我虽不是社会等级中的弱者,但我是资本洪流中的弱者。资本的噪音正在肆无忌惮地剥削着我的身体健康、压榨着我的听音自由,而我却对此无能为力。我有听音自由吗?
以对称性原则来看,与这个问题相对应的另一个问题是:制造噪音是个体的自由吗?
经常有人在电梯、地铁、餐厅中大声说话,仿佛这个公共空间是他(她)的私人空间,如果你制止,他(她)会反驳:“这个电梯是你的吗?这是公共空间,我有发出声音的权利!”这就涉及声音与隐私空间的问题。在公共空间如何把握个人的活动空间和他人的隐私空间,往往是一种道德约束。日常生活中,制造噪音的行为是一种不道德行为。在图书馆要小声说话已成为一种共识,进入图书馆的人会下意识地放低音量,把手机静音;在博物馆、音乐厅等正式场所里大声喧哗会有工作人员来提醒;但是在电影院里基本上就全凭自觉了,我曾不止一次在电影院里遇到不停接电话的人,也曾多次在飞机、高铁、公交车上被邻座的高分贝声音侵扰,仿佛整个公共空间都是他们的表演场域。
在公共空间小点儿声,是个体对自己制造噪音的权利的一种限制,这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素养。这种道德基于对他人听音自由的尊重,这种素养基于对隐私空间和公共空间两者间关系的把握。在一个四处充斥着资本噪音的时代,管好自己所发分贝或许是个体唯一能做的坚守。
哲学家思考的一个终极命题是:何为良好生活?苏格拉底言:未经反思的生活不值一过。古往今来诸多哲学家对人类生活进行了反思,然而从声音维度来思考的并不多见。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发问,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是看鸟飞花开更重要,还是看手机看电视更重要?噪音问题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维度:是听鸟鸣树摆更重要,还是听装修听车跑更重要?是享受安静的睡眠和散步更重要,还是听商场、餐厅高分贝的背景音乐更重要?
你想要生活在一个声景是何样的世界?
共有 0 条评论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